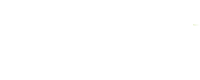夏可君|与南希告别:斯特拉斯堡之心 拜占庭余晖:纵横捭阖下的人性纠缠,中世纪的黑暗时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夏可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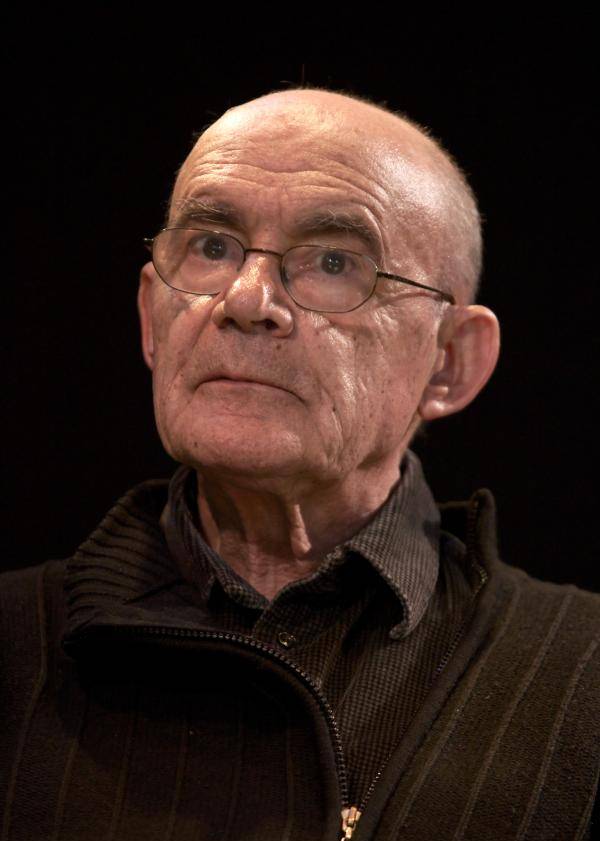
让-吕克·南希(1940.7.26-2021.8.23)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2021)于当地时间2021年8月23日晚上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让-吕克·南希,1940年7月26日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1962年从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毕业, 1987年获得国家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有德里达、利奥塔等。1988年开始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接续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以共通体的非功效、基督教的自身解构、世界的意义与身体的触感,扩展了解构的论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曾赴斯特拉斯堡跟随南希学习,他撰文纪念南希。
再见,再一次,我重复这个言辞,最后一次,对你说:Jean-Luc,Salut,再见!
是的,总会有告别的那一天,无论用法语说,还是用汉语说,但自此后,永远不可能,面对面地说:再见!这是余存的我们最大的悲伤。
这是最大的悲伤,自此,永远,不再可能与你,面对面,说:再见!
是的,死亡会来临,现在,死亡是在场,自此,余存者不得不与死亡共在,但与死者的共通体,不就是你所言的不可能的共通体?那非功效的或无用的共通体?但自此以后,不再有慰问,不再有见面,不再有回应,剩下的,仅仅是泪水遮住的余像。
而死亡总会来临,死亡总是会提前,无论哲学如何提前练习死亡,无论哲学如何学习哀悼的艺术,但对于你,就如同德里达所言,死亡已经被延异了,三十年的心脏移植手术,已经是奇迹,你已经是余存者,一直都是余存者。每一年的5月,我们都会特别担心,你都会去医院疗养,但今年却是8月,这一次,是两颗心脏的死亡,不,是三颗心的死亡,我们的心,斯特拉斯堡之心。
此刻,斯特拉斯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夏可君编校的《解构的共通体》(2007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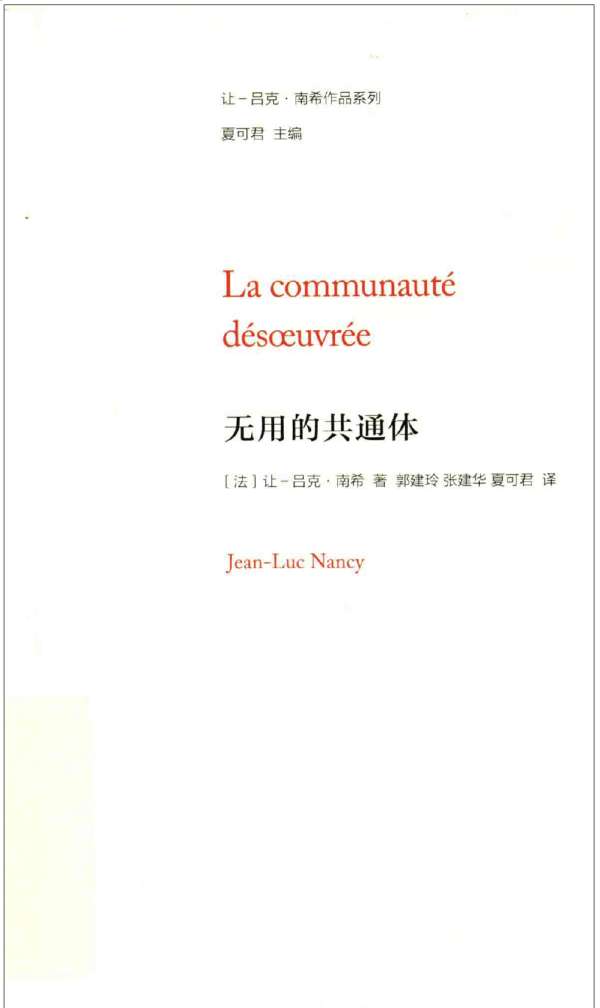
夏可君参与翻译的《无用的共通体》(2016年出版)
对于一个同时在莱茵河两岸都漫游过的中国哲学家,德国的弗莱堡是现代哲学的梦想之城,无数的外国留学生都去往朝圣,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却是哲学的友爱之城,是解构之心脏最为隐秘的跳动之所!如同德里达在去世前不久,在斯城,面对自己最为钟爱的两个学生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与让-吕克,衷心地赞颂“斯城”乃是伟大的友爱之城,是友善的见证之都,因为斯特拉斯堡不仅接纳过很多的流亡者,斯特拉斯堡也是解构之城,以至于后来德里达建议,可以把斯特拉斯堡大学,改名为Lacoue-Labarthe-Nancy大学。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从弗莱堡到斯特拉斯堡,乃是由老一代的布朗肖和列维纳斯所开启,以德里达与利奥塔在斯特拉斯堡的多次研讨会为中介,在拉库-拉巴特和南希那里得到深入的展开与扩展,直到年轻的一代建构起“欧洲哲学议会”。当然,如果想到埃克哈特大师也曾在此漫游,歌德也曾在此学习,斯特拉斯堡才是真正的解构之城,是欧洲哲学自身解构的心脏。
布朗肖著《不可言明的共通体》
我参观过欧洲议会大厦,那由地球仪建构的大厅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共通体,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斯特拉斯堡真正成为欧洲的中心,那可能才是欧共体,不,是南希时所言的“欧洲共通体”,真正发挥历史伟大作用的开始。
我与几个在斯特拉斯堡学习过的朋友,经常喜欢戏谑地称我们为“斯派”的中国传人,在德国与法国的思想文脉中,即,除了在德国与法国哲学的差异之间,“斯派”的思想气质同时也是一种在哲学理性与犹太信仰之间(包括基督教),隐秘滑动着的悖论张力,这是心之割礼,是心之开裂,在分裂中的艰难共在,在爱之中的分裂,如同南希对于这两个传统与四个方面的深度整合:
把列维纳斯的他者转换为“共在”,把布朗肖不可明言的共通体深入到“分享”,把德里达的延异间隔扩展到敞开的“空无”,把海德格尔的敞开扩展到神性来临的“通道”,当然还有浪漫派与尼采的“片断”写作,南希是最好的“欢愉化”实践者……无论是基督教的“自身解构”,还是“触感”的生命技术,南希的思想所关联起来的思想平台或者解构空间,即“世界的可能性”,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上触发即将来临的可能意义,尤其是在病毒全球化之际,人类与病毒的长期的可能共在——不就需要文明再一次深入阅读南希的思想?!
南希与夏可君在2003年第一次相遇
我这样在南希家里学习过的人,可算是所谓的入室弟子了。2003年我在弗莱堡学习,但与南希的见面却是在海德堡大学,本来是德里达去海德堡要作“伽达默尔讲座”第一回的,但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成,不久南希去了,我特意去听了他关于德里达的讲座,黑板后面的法语词“différance”(延异),成为了我与南希,以及解构的心传密码,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到德里达的技术化“延异”,再到南希的“它异”感发,我自己则试图走向庸用论的“诡异”。
后来德里达去世,我就决定去法国斯特拉斯堡跟随南希学习,选择南希,也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海德格尔的世界问题,而灵感其实来自于南希的《世界的意义》(Le sens du monde),因此,思考世界如何可能被给予,世界如何再次获得存在的意义,人性如何在一个不再共有的世界上如何共在,就成为我与南希思想对话的出发点。2005年那个时候,南希已经从大学退休了,我就大约每一周去他家里一次,那条路,从我居住的大学到他居住的街道rue Charles Grad都还历历在目,拿着德里达与他的书,用法语讨论一些具体的段落,有时候也聊一些相关的思想,会经常留下来一起午饭。有一次,他特意让我见了他和海伦的孩子,南希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大师,似乎是担心我想念中国,特意拿出一个地图,问我的老家在哪里。我回国十年左右,2015年7月本来去斯特拉斯堡再次拜访他的家,但可惜他去度假了,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我们经常通邮件,深入讨论过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围绕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是否发生过,我们有过很多次的通信,甚至争论。而且最近几年,我都会在11月寄给他一本故宫的艺术台历,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寄,这就意味着,每一年他都还在……
南希与拉库-拉巴特合著的《文学的绝对》
在南希七十岁的一个小讲座中,他已经说到了离开与告别:
“离开,是死去一点点;死亡,是完全的离开。”“离开,是死去一点点”,因为在每一次离开中,我们都感受到难受、痛苦,某种东西消失了。当某个人死去,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在场本身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不再在此处,他经由我们在其他时候所说的“最大的离开”走开了。我们经常说那些死去的人是离开了,这是委婉的措辞,用以弱化不可避免地包含在动词死去和死亡中的痛苦:不再返回的离开。
同时,死去之人的某部分保留在某处,在我们之中,与我们一道,因为在他们身后余存的我们是那些离去之人的所有部分。我们以这种方式守护着他们。
——是的,我们这些余存者就在守护离开的朋友,每一次都是唯一的、整个世界的终结,并且,只有这一个世界,我们所守护的只是还留给我们的这个唯一的世界,充满忧伤与创伤的世界,但我们不得不更为加倍地珍惜这剩下的世界,守护朋友的离开,守护他的彻底告别。
但这是哀悼的时刻,不适合详细地分析,回忆的泪水温暖那些相遇的时光,是的,我们不可能再见了,只能在文字中哀悼,在文字中书写曾经的共在。
再见,这还是相遇,Jean-Luc,这是在你的未来,我们与你相遇,把你对于法语最为细腻的心感,对于生死的触感,带往一个异域的未来,解构的力量在于打破同一性的逻辑,“不只一个”(Plus d’un),总会“余出”另一个的开口与通道,打开相遇的机会,打开汉语思想中的未来,就如同德里达在写给你的最伟大的后期著作《触感,让-吕克·南希》(Le toucher, Jean-Luc Nancy)中的最后一句:
Un salut sans salvation, un salut juste à venir.
请过来,来到汉语中,如同你的很多著作我们已经翻译出来,等待出版,你将与更多不知道的读者相遇,那是事件的惊讶,是世界的可能性。
附:已出版的让-吕克·南希著作中译本
《变异的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
《解构的共通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文学的绝对》(与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合著,译林出版社,2012年)
《我有一点喜欢你:关于爱》(新星出版社,2013年)
《不可能的正义: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新星出版社,2013年)
《天与地:关于神》(新星出版社,2013年)
《肖像画的凝视》(漓江出版社,2015年)
《文字的凭据:对拉康的一个解读》(与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合著,漓江出版社,2016年)
《素描的愉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无用的共通体》(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责任编辑:丁雄飞
一个人活到百岁,眼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特别是晚辈,其内心其实是比较难受的。然而,每个人都想活着。一个朝代更是如此,虽然坐在宝座上面的人未必心情舒畅,但那种一言九鼎的威风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所以,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有势力的人仍然对此趋之若鹜。对于11个世纪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来说,只要能够披着这个旗号,怎么活着都行。马其顿王朝的威风已成往事,杜卡斯王朝在走马灯式的变化中,在1081年迎来了最后时刻。
阿列克塞的忧愁
面对着1071年后的战败,阿列克塞一世这位年轻的帝王筹划着该如何度过难关。虽然他有着军事才能,但战争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事情,还要靠军事资源。如今,军人的主要来源地小亚细亚已经被塞尔柱突厥占据,紧靠毫无忠心、善变的雇佣军来对阵强大的突厥人,阿列克塞一世觉得根本不可能。

为此,他想到了联合。但是,在这个已经乱了千年的世界,阿列克塞知道:就是兄弟姐妹,在干事情的事情都要给好处,更何况比敌人还要善变、还要凶险的亲戚。所以,阿列克塞决定给对方一个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礼物。对方要做的就是出人出兵替他抵挡突厥人的铁蹄。
与“兄弟”的联合
众所周知,基督教分为三大派: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基督新教正式成立于16世纪,而这时还是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天下,新教徒们还在形成过程中。
基督教的东方教派以新罗马城(君士坦丁堡)为核心,西方教派也就是今天的天主教以罗马为核心。双方从公元5世纪开始就一直在为“谁是老大”在较量,从暗中的、不伤面子的较量,直到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
东方教派实力壮大,是随着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增强而逐渐壮大的。在基督教五大主教区中,东方教派就占有四个,分别是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罗马。其中君士坦丁堡在5世纪,因为拜占庭的缘故才得以跻身大主教区,以前是四个。罗马也是因为罗马帝国首都所在地的缘故。所以,其根本仍然是权力使然。

那么,作为罗马教皇,当然希望基督教重新统一在自身领导下。这是罗马教宗们梦寐以求的伟业。科穆宁王朝的阿列克塞一世决定,以这个为条件吸引罗马帮助自己吸引几万雇佣兵前来帮助自己保护拜占庭帝国。
乌尔班二世很积极
对于来自东方的橄榄枝,阿列克塞一世答应将东方教派重新归属在罗马治理下的条件太诱惑人了。教皇乌尔班二世立刻行动起来,罗马教廷开始尽全力配合。
作为教皇,乌尔班二世也深谙人性。如果想让别人去做什么,必须要给与对方好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必须要给。因此,乌尔班二世策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讲述了基督教的东方兄弟身处在苦难中,只要西方的兄弟们愿意挺身解救他们,那么,他们现世的一切罪孽都将消除,结束现世的苦难、凶残后他们将进入天堂享受一切。

对于今天看来,这种许诺很熟悉。然而,这对于黑暗的中世纪来说,千年中世纪的人们绝大部分都有一种罪恶感。不断的战争必然伴随着抢掠、凶杀甚至背叛、盗窃,每个人要想活着都离不开“恶”的一面。因此,中世纪的教徒们有着一种深深的“赎罪感”。
当然,这种“赎罪感”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入夜后,人们在风云之后的喘息休息中产生;也许在酒足饭饱后仰望星空中产生;也许在背叛了兄弟情、朋友情之后拿着报酬的欢乐中产生。
贪欲主导着这一切
但是更多的人的“罪恶感”,只是停留在产生的片刻。更多的人在面对着财富的时候,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伴随着“罪恶感”,在没有现世快乐的恐惧下,他们同样把自己的刀剑伸向了自己的东方兄弟。从东征一开始到结束,这种事情很多很多。
但在当时,在听乌尔班二世的演讲时,人们迸发的“罪恶感”却是真实的。人们非常踊跃地参加了战争,无论是贵族还是骑士或是农民、手工业者,人们都涌向了君士坦丁堡。面对这一切,阿列克塞一世有些惊慌,乌尔班二世很后悔自己的演讲太给力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给予束缚。
乌尔班二世命令罗马的主教们去乡间、去城市告诉疯狂的人们,地还是要种的,农民还是要种地的;工匠们还是要工作的,商人们还是要做买卖的。
阿列克塞一世则调动帝国的军队,对前来抢掠、袭扰帝国臣民的西方支援兄弟不要客气。为此,东征的这些西方兄弟很是愤怒,认为东方兄弟对敌人对自己还要好。就这样,仇恨埋在所有人的心中。延烧两个世纪的东征在末期又迎来了东方一股更强大的势力,伴随着蒙古大军的到来,无论是基督教世界还是伊斯兰世界都处在混乱中。
但无论怎么混乱,有一个主导因素永远不会改变:人性对物质的贪欲。
拜占庭悲歌:复活资源已无,盖世豪侠科穆宁徒留一声叹息
朱元璋的禁海政策符合当时社会,朝代的合理性与安全性
俄罗斯为克里米亚进攻拜占庭,被突厥偷袭后头骨做成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