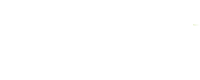记忆,是一个人内心的疆域。若要在其中漫步,需要依靠地标,才能时时确认自己的方位。对65岁的秦文君来说,她的地标,是外白渡桥。
3岁之前,几乎每一天,她都被抱着或者牵着从桥上走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最初的依恋,在此萌生。17岁之后,她离家千里,外白渡桥成为她怀念家乡时,一个具体的寄托。
在相隔两地的日子里,她若能回到上海,必定要看看这座桥。手抚桥钉,听江声滔滔,似乎在祝福故乡的家人安好,也似乎是从中汲取力量,来不断确认自己从哪里来,未来要到哪里去。
人的依恋
因为历史的机缘,南下干部父亲,和家住老城厢的母亲,在上海相识相恋。因为地势的机缘,起于北新泾的苏州河,和起于淀山湖的黄浦江,在外白渡桥下相交相会。像那个巨变的时代里,无数新生的事物一样,新婚的小两口,把家安在外白渡桥边的大名路上,诞育了新的小生命。
1954年,秦文君出生在父母位于大名路的房子里。满月之际,按照本地风俗,新生儿要被抱着“过桥”以求长大后平安勇敢。父亲就抱着长女过了外白渡桥。
待秦文君满月后,母亲恢复上班。母亲工作单位所在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处总部在中山东一路的太古大楼,母亲所在的联合采购部在圆明园路上。单位为解决女职工后顾之忧,设有哺乳班,可以托送婴儿。每天清早,母亲从大名路的家出发,抱着秦文君穿过外白渡桥去外滩上班。母亲雇来的小阿姨蹦蹦跳跳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婴儿用品。阿姨一路逗着婴儿,婴儿一笑,母亲也笑。外白渡桥属于笑声。
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南昌路一机部的宿舍住。此后每每经过外白渡桥,秦文君觉得,算是回到“故乡”。
母亲有一次带秦文君在桥下的小西餐店吃西餐,这是秦文君第一次吃西餐。她记得手握刀叉的触感,也记住了这座桥和周边建筑所呈现的异域风情——和外婆家位于南市老城厢的建筑完全不同,展示着另一种文化的密码。
渐渐长大,无须再被大人抱在手里,秦文君自己从桥上走过,有时会在桥板上捡到一些东西。有时是一颗生锈的小铆钉,有时是一枚玻璃弹子,玻璃弹子上留着神秘印痕。她把它们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将之与全钢结构桥身上的铆钉比对,这不是桥上掉下来的零件,但却像桥梁和她有默契,偷偷藏在这里,等着赠予她的小礼物。
就像一棵村口的老树,特意备下果实,等自己珍爱的孩子去发现。
图片来源:钟昱 摄
故乡的影像
1971年,秦文君17岁了,即将随时代的安排,赴黑龙江上山下乡。离别之际,她告别亲友,也到外白渡桥和它告别。外白渡桥周边,已经没有她的家人居住,但外白渡桥本身,对她而言是一个朋友,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身影、气味、温度和一切。
此后直到1979年回到上海,漫长的8年里,秦文君每次从黑龙江回沪探亲,都会去外滩独自到外白渡桥走一走,或者在附近坐一会。探亲的时间多么短暂,但秦文君总不吝啬把时间留给这位旧知。“坐在那里,看着车来人往,觉得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都有自己的位置,只有自己没有位置了。但是心里面的外白渡桥还在,总感觉它老,它懂。”
在那段岁月里,外白渡桥是否常常会打喷嚏?因为那些奋斗在外的上海知青,都很想它。
在梦里,桥身在晨雾中慢慢清晰,整个外滩建筑群展现眼前,江面上传来的阵阵汽笛声,过往电车上的“小辫子”颤颤巍巍,偶然闪烁火花,发出滋滋声音,还有无数车轮滚动的声响和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构成一种属于上海的声音,在黑龙江的冷夜里,在安徽、在江西、在云南、在贵州的某个角落,回响在许许多多知青思乡的梦里。
图片来源:新华社
桥的故事
差不多在秦文君出生100年前,1856年英商韦尔斯等组织苏州河桥梁建筑公司,在此建一座木桥,称为韦尔斯桥,来往行人车马过桥均要付过桥费。
1872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在桥西另建一木桥,长117米,宽12米,并将已陈旧的韦尔斯桥收购拆去。因新桥位于外滩公园旁,故称公园桥;又因此处原为外摆渡处,亦称外摆渡桥。因过此桥已经不再收过桥费,逐渐被大家称为外白渡桥。1907年,工部局将此桥改建为钢桁架桥,长104米,宽18米。下部是设有木桩基础的钢筋混凝土墩台。二孔,能通航,成为城市标志性构筑物。(《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08年4月6日上午,百年老桥外白渡桥将接受为期一年的体检,驳船托起桥身,南跨桥体借着黄浦江涨潮浮力,缓缓起身并在水面上转身,于12时05分正式出航,驶向“体检和疗养地”——上港集团民生分公司码头。当日外白渡桥附近的水面封锁了交通,附近的道路也加强了交通疏导,毗邻外白渡桥的黄浦公园采取了限流措施,增设了围栏,但看台上挤满了热情的观众。外白渡桥北侧的上海大厦里,也有不少人探出头来,俯瞰大桥。2009年4月,整修好的外白渡桥归来时,又引发许多市民冒雨等候。
有多少上海人,就有多少个与外白渡桥有关的故事。
图片来源:张海峰 摄
1899年,11岁的顾维钧考入上海英华书院。一次经过上海市区的外白渡桥,顾维钧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拉车上桥本来就很累,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愤怒地斥责他:Are you a gentleman?(你算不算个绅士?)暮年时,这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外交官告诉子女:“当时我年岁太小,并不理解政治变革,但我能感到,有些事很不对劲,有些事应该得到纠正。我从小就受到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决定今后要从事外交政治。”
在1932年和1937年两次战争中,从虹口、杨树浦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主要聚集于外白渡桥,希望由此进入公共租界避难。日军占领上海后,外白渡桥北岸由日军把守,南岸则是公共租界的属地。人们往来于虹口与公共租界之间,都须提供通行证,并接受搜身,还须向日本士兵鞠躬,许多上海人往来桥上,都曾遭受日军的耳光和拳脚侮辱,这也成为一代上海人的耻辱记忆。
70年前的5月25日上午8时许,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部队打到苏州河边,却都在桥边受阻于敌军强大的火力封锁。最先到达外滩外白渡桥的是27军79师235团1营。打头阵的战士尚未冲到桥中央,就全部牺牲。鲜血染红了苏州河。
当曾在部队服役的父母,抱着诞生于和平年代的秦文君走过外白渡桥时,是否想起过牺牲的战友?当少女秦文君一次次流连在外白渡桥上时,是否也感受到了城市历史中先辈走过的足音?
而一代代人来来往往,桥始终在那里。每一个清晨,迎接游客、迎接上班族、迎接拍婚纱照的新人,也迎接某个被父母珍爱抱在怀里的满月孩子,郑重走过这座桥。这是它欢迎一个新生市民的方式。而小孩睁开眼睛,记住了跃入视线的第一个鲜明的城市地标。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