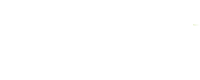从前有个小媳妇,她年轻时先后生下六个孩子,都没站住。到了四十岁那年,好不容易又生下一个儿子,但是丈夫却去世了,儿子成了她独一无二的命根儿。冬天,她老早为宝贝疙瘩穿上皮袄。夏天,她手不离扇地为儿子扇风。
她奶水不足,她上山挖来山铃铛根打粘糊糊,嘴对嘴地喂他儿子。儿子小腿会站住了,她一步两步三步教他学走路。儿子渐渐懂事了,学会了骂人和打人,她舍不得说一句,怕委屈了她的心头肉。
这位讷讷忍饥受苦,一年年地头发白了,儿子也无忧无虑地长大了,可恶习也一天天地养成了。左右邻舍送给他个外号、叫“鹗依痕”,就是毛驴的意思。鹗依痕祖上留下几亩地,靠种地为生。他在地里干活,他讷讷给他送饭。送饭早了,他顺手就给讷讷一顿赶牛鞭子,嘴里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老太太,谁让你这么早送饭来,我还没饿呢!”送晚了,他伸手冲着讷讷就是几撇子,一边打一边说:“你这个老糊涂虫,来得这么晚,我把饿坏了!”打得他讷讷见着他胆怯怯的,只好背地里擦眼抹泪,悔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管教。
一天有鹦依痕干活干累了,在地头上的一棵大树底下脸向着天,躺在树下歇息。这时就见树上有个老鸹窝,窝沿上露出一排小脑瓜。一只大老鹬扇着翅膀,嘴里叼回一个虫子,一排小脑瓜小嘴一齐“加加”着要食吃。大老鹬把虫嘴对嘴喂了一只,喂完又飞走了。不一会儿返回来,又嘴对嘴喂第二只。
大老鹬也不知飞了多少个来回,一排小脑瓜都喂完了,才飞进窝里,膀子一张,把崽子都抱在膀下。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后,鹗依痕又在树下脸冲天歇息,他见小老鹬扇乎着翅膀,嘴叼个虫,飞回窝,把虫嘴对嘴喂给窝里的大老鹬。大老鹬吃了虫,小老鹬飞走了,不一会儿又叼回一个嘴对嘴地喂。鹗依痕先是见大老喂小老鹬,心想,老鹬养活儿女真不容易,吃了这般辛苦。后来见小老鹬喂大老鹬,心想,动物还知道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一个人怎么还不如禽类?
鹗依痕长了二十来年,终于寻思过味来了。这天,见他讷讷又来送饭,大热的天,脸上冒着汗,走得挺费力气的。他长这么大头一回来了孝心,顾不得放下手里的赶牛鞭子,就去接讷讷。讷讷寻思这饭不是早,就是晚,又要挨鞭子抽了,磨身就往回跑。讷讷在前面跑,鹗依痕在后头追,眼看追上了,讷讷心想,总挨儿子打,活个什么意思,干脆死了吧。正好前面有棵大柳树,她一头撞在大柳树上,碰死了。
鹗依痕见讷讷死了,好一顿哭,怎么哭也哭不活了,就把柳树砍下来,扛回家,按他讷讷的模样做成一个人,供在西墙祖先位旁边。他不知怎样才能赎罪,每逢年节,都把讷讷生前喜爱吃的黄米饭,供在木头人面前。
供一次,鹗依痕心里难过一次,看看木头人,木头人好象用眼睛在责备他。鹦依痕怎么也排除不掉心中的悔恨,总觉得木头人用眼睛在责备他。渐渐熬糟病了。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身上瘦成了一把骨头。眼见不行了,便对木头人说:“讷讷,我对不起你,我没有脸再活在世上,让我死了吧!”他又叫过自己的媳妇,说:“我死了,逢年过节,千万不要忘记了供奉讷讷。”媳妇说:“你放心吧,我供奉就是了!”鹗依痕听了媳妇的话,点了点头,死去了。
这媳妇从进婆家门,就见丈夫对婆婆今儿打,明儿骂。她本来嫌弃婆婆,就和丈夫拧成一股绳,给婆婆气受。等到丈夫醒了腔,她还照样坏。丈夫临死前嘱咐她供奉木头人,她嘴答应得挺快,心里却骂道:你这个老死太太,活着的时候咱们白白养活你,死了还把我男人带走了,看我收拾你!她心里骂着,随手拿起做针线活的针,把木头人十个手指头,一个扎一个眼。光扎还不解恨,又举起手打木头人的嘴巴子。
一天,她正打着,突然一股火苗从灶坑里窜出来,“忽啦”烧着了小草房,把她活活烧死了。左邻右舍跑来救火,只见到地上剩了一堆灰。那灰里没有金,没有银,只有一个木头人。
人们说,木头人是柳树做的,柳树是神树,是不怕火烧的。从这以后,满族人便崇拜起柳树来了。称柳树为柳树讷讷,把她请到家里的祖先位置旁边。那些虐待老人的儿女,见了她就心惊胆战,再也不敢不敬不孝了。满族人尊老爱幼的习惯也从此形成了。在满人家里柳树讷讷便被奉为保佑子孙兴旺,家宅平安的神。